3月14日晚7点,“月旦读书会·仲春之月”成功举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邓建国教授受邀为师生们导读其最新译作《奇云·媒介即存有》。9001cc金沙以诚为本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夏维波、副院长田静,青年教师潘晓婷和崔琳作为本次读书会的分享者,黄品嘉担任主持人,参会的校内外师生共二百余人。

《奇云·媒介即存有》是由美国当代著名媒介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哲学家约翰·杜海姆·彼得斯所著。此书历经5年创作,4年翻译,1年出版,横跨十余个学科。邓建国教授的译本从标题到内容,准确流畅,译注丰富,语言幽默,可读性强,是继同样为彼得斯所著、邓建国教授所译的《对空言说》之后,又一本当代媒介研究领域极具参考性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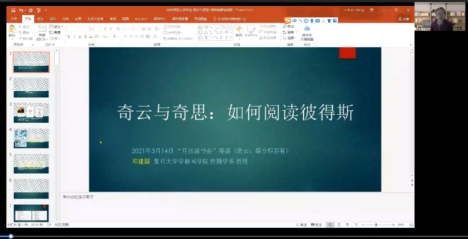
邓建国教授线上领读《奇云》
邓建国教授首先进行了领读。他说这本书是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一部著作,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彼得斯认为,元素型媒介是能够操控和管理时间和空间的东西,代表着各种秩序。彼得斯把媒介扩张到文化技艺这个层面,这一技艺可以按表层/底层、古代/现代两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由此邓教授探讨了媒介考古学的渊源、“技术”一词的多语种多角度含义,阐释了哲学人类学的方法、本雅明式的历史勾连法、思想实验法等研究方法。邓教授介绍了彼得斯的写作渊源,即受到“人类世”和“后人类主义”的影响。彼得斯延续了欧美媒介研究中的“技术性传统”,将媒介视为“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他深受海德格尔和基特勒思想的影响。邓教授将海德格尔的媒介技术观念、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与彼得斯的媒介哲学分别进行了对比。最后着重分析了彼得斯给我们的启发。他认为,从《对空言说》到《奇云》,彼得斯完成了从传播的认识论到媒介的本体论。此外,传播研究需要更多如彼得斯一样的“生成性思想”和进行“知识大融合”。他强调“传播学者不仅要做科学家,而且要做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
随后,几位分享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奇云》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潘晓婷老师着重分享了自己对媒介研究领域中的媒介到底是什么的理解。她认为,首先彼得斯说媒介是占据中间位置的“中间之物”,其判断标准是它创造了人的生存条件。但是彼得斯并没有让这个概念由此划向一个绝对泛化,因为他还强调个中间位置一定是现象学的,具有主体特异性。所以彼得斯的媒介是有边界的,那就是它是否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的中间之物,它是否为人创造了一种在世存有的条件。其次,彼得斯说媒介是基础设施,它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这一点主要是为了对各种新旧媒介进行祛蔽,对媒介运作方式的祛蔽,也是对这个世界的祛蔽。第三,彼得斯谈到媒介是人工物和自然物的结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中谈到,普罗米修斯为人间送来的火种,它代表的技术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就是技术的人。《奇云》这本书解释的媒介概念下的本质性意义,即揭示了它作为基础设施的意义。由此,媒介这个概念可以以基础设施的身份重新整合过去、现在或者未来可能会有的成果。
崔琳老师认为,人们在理解“媒介”这一概念的时候往往会采用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即用惯常的方式作出理解和解释。这是由于人们深受当下媒介环境的浸润,不能跳出既有思维来认知媒介。彼得斯从反思(哲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媒介”进行考古,通过历史和时间中的经验和事实来重新理解人类当下的境况,为我们展现了人类与媒介相融共生的景象,揭示了人与自然、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了被人们忽视的另类历史。她还指出:在媒介考古学领域,德国学者常以技术——硬件为导向,强调技术是一种“原初动力”,彼得斯在《奇云》中对技术的探讨也受到海德格尔、基特勒的影响,强调技术的本体性和物质性,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基础型媒介”“后勤型媒介”“元素型媒介”等概念,视角极其独特,视野极其开阔。在方法方面,虽然彼得斯并未宣称《奇云》采用了媒介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但彼得斯对媒介的思考和研究为媒介考古学这一新兴的研究形式带来了诸多启迪,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田静副院长也分享了自己对彼得斯媒介概念的理解。彼得斯将媒介这个词从信息传播中解放出来,将媒介看作是使用者创造的生存条件,使媒介的概念从讯息层面拓展到了栖居层面。她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关系,自然作为人生存的环境,对生命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人作为被塑造的产物,是按照自然所塑造的方式来存在的。“人类的生存依赖于各种对自然和文化施加管理的技艺”,而这些技艺都以“元素型媒介”为基础。基础设施为人类的存有提供了潜在的背景和条件,搭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框架。它所发挥的作用是辐射式和传递式的。它成为了人类生存的构成性要件。人类的存有早已借助技术而人工化。她认为,彼得斯研究视角和对媒介概念的扩展,为媒介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彼得斯还认为媒介理论应该是一门后学科,跳出某一单一领域,进入元领域,将系统性的看待世界作为视角。这些是《奇云》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此外,她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疑惑,如彼得斯“媒介”是否成为了他将人的存有与自然环境连接在一起的“中间之物”的工具?到底什么是最终极的基础和元素,判断标准是什么?彼得斯的媒介研究还可以怎样发展?对媒介外延的扩展和追问是否会动摇彼得斯“媒介哲学”的基础?媒介研究的边界到底在那里?
夏维波院长读书分享的题目是《北冥有鱼——<奇云>中的概念棋局及其互文性与解释力》。他首先从写作学的视角认为,彼得斯强调海德格尔情愿牺牲他的“王后”——知的自我——这个现代哲学中最强有力的棋子(概念),是为了保持其“存有”(being)和“物”(thing)这些哲学棋子,直到最后将军,彼得斯“元素型媒介”和“媒介即存有”等概念“相加”和“推进”,即是理论棋局。单谈元素型媒介便停留于芒福德、英尼斯、基特勒等媒介环境学派的互文话语;单谈媒介即存有没有跳出海德格尔“此在”“座架”的强大的解释域,而两者相加接力则构成新的理论解释力。“元素型媒介”与“基础设施型媒介”和“后勤型媒介”的概念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媒介“环境”与“透明中间物”两重含义的关系推进。“元素型媒介”即环境和容器,“基础设施型媒介”和“后勤型媒介”两个概念把“元素型媒介”的内涵缩小为“居中状态”的媒介,彼得斯继而从狭义的媒介技术视角和更大的生态学视角,来分析媒介与技术和自然与人工两个方面的居中状态问题,这样就把“媒介环境”转化为“环境媒介”。三个概念是“由大到小,由小到大”的推演。基于概念的“相加”和“推进”,《奇云》即完成媒介讨论话语的互文,也形成自己概念体系的解释力,同时更在学术视野上超越了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斯诺命题”。作为一种媒介哲学,《奇云》借助德国的文化技艺思想把技术与自然的复杂而偶然的“折叠”作为自己本体论,这既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呼应,又避免了“平本体论”的简单化。在认识论上,彼得斯吸纳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思想,周遭世界具有预设性和遮蔽性,这与“居中状态”的隐蔽性是相通的。萨弗兰斯基认为海德格尔使用了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手法来强化对“日常世界”(周遭世界)的分析,而夏维波基于此认为《奇云》从鲸鱼、大海、天空、大地等角度谈元素型媒介,既是一种生态学视角也是一种陌生化手法。其本意不在于其不熟悉的生态学,而在于当下的媒介技术本身。在价值论上,《奇云》既然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便不能对媒介之利害持简约化的立场,而是基于“零”或“云”的本体论模型做开放性的价值隐喻。